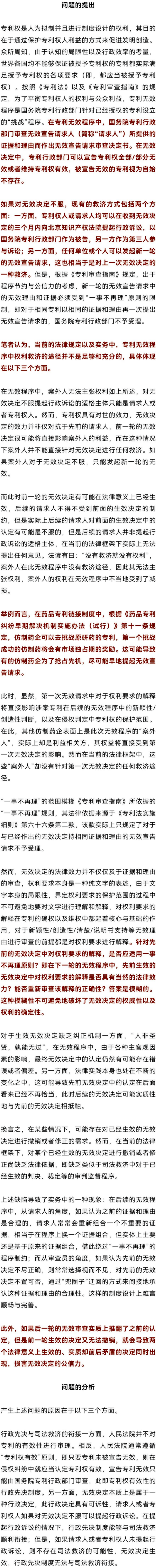
当事人处置原则与公众利益的矛盾当前的无效程序以当事人处置原则为基础,以合议组依职权审查为例外和补充的框架。通常情况下,请求人所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而非公众利益。出于种种原因,例如达成和解、专利权人在无效程序中的意见陈述使得请求人的产品不落入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考量成本和时间等,针对一个对于专利权人有利的无效决定,请求人并不是每次都积极地尝试救济。然而,专利权的效力是对世效力,实际上涉及到一般公众的利益(这也是《专利法》将任何单位或个人都确定为提起无效宣告请求的适格主体的原因),更加涉及到与涉案专利所保护的发明创造有直接商业联系的相关方的利益。举例而言,如果一项药品专利得以维持,则无疑对仿制药企设置了巨大的障碍,从而间接地提升了药品的价格,影响到一般公众的利益。无效程序中的当事人处置原则与专利权涉及的公众利益之间存在矛盾。
效率与实体公正的双重考量法谚有云:迟到的正义非正义。借助于法律来实现正义的时效性是重要的,理应尽快定纷止争、维护合法权利,结束相关方的不安状态。进而,司法资源显然也是有限的,不可能将无限的资源投入到一个案件。而自然辩证法又告诉我们,对真理的追求是无穷无尽的。资源的效率与实体公正具有天然的矛盾性,不得不进行折衷。问题的解决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尝试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提出一些可能改进的方向。
案外人主张权利《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提起诉讼,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可以参与诉讼,以及这两种“第三人”在一定条件下对于生效的判决、裁定等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行政诉讼法》中也规定了“第三人”的参与诉讼以及上诉的制度。虽然《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第三人”的概念与专利无效程序中的“案外人”并非毫无二致,但如前所述,专利权具有对世效力,没有任何单位或个人能够真正置身“案外”,一般公众都是专利权的“第三人”。因此,从制度设计上来说,设立针对生效无效决定的“案外人”撤销之诉,或者针对作出的无效决定为“案外人”设立独立的诉权,有一定的合理性,这可以赋予“案外人”相对独立的诉讼地位与司法救济途径。
生效无效决定的撤销制度生效无效决定的撤销制度,实质上是对于生效无效决定的“监督”程序。如前所述,在目前的法律实践中,修改或者推翻生效的无效决定没有法律上的依据。据此,可以考虑下面的制度创新:从行政路径上来说,无效决定本身是一种行政行为,可以通过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提起行政复议或者申诉的方式,来请求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重新作出决定;从司法路径上来说,可以通过向人民法院或者人民检察院提起申诉的方式,来请求人民法院对无效决定是否合法进行审理,从而撤销原先已经生效的错误决定,并且要求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重新作出决定,由此实现对生效无效决定的行政监督救济或者审判监督救济。法院对“一事不再理”的实体审理如果考虑立足于当前的法律实践,以变更较小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笔者建议:对于不服“一事不再理”的诉由,不仅仅赋予人民法院审理“一事不再理”的程序是否合法的职权,同时赋予人民法院审理实体是否合法的职权。具体而言,设想这样的场景:在第一次无效程序的无效决定生效(例如,维持专利权有效)之后,在后请求人仍然以相同的证据和理由提起无效宣告请求;在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以“一事不再理”为由不予受理之后,在后请求人对“不予受理”的决定不服而向人民法院起诉。在此情况下,可对人民法院的职权进行如下变更:人民法院不仅仅审理“不予受理”的决定是否合法,也有职权审理此证据和理由究竟能否成立,即第一次无效程序的无效决定是否合法;如果认定第一次无效程序的无效决定违法,即此证据和理由能够成立而专利权应当被依法无效,则人民法院能够撤销原先已经生效的错误决定,并且判令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重新作出决定,由此通过对“一事不再理”的审理,实质上对先前生效的无效决定进行“审判监督”。
总结而言,在目前的无效程序以及后续关联的司法程序中,专利权人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一方面其几乎不需要承担举证责任,另一方面其也不会被排除在程序之外,而可以充分地主张和救济自己的权利。然而,在后的请求人可能由于先前请求人的无效请求而面临不必要的约束或障碍,承担了过多的负担,且有时难以主张和救济自己的权利。据此,“案外人”的参与、生效无效决定的撤销以及法院对“一事不再理”的实体审理,是笔者建议采用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