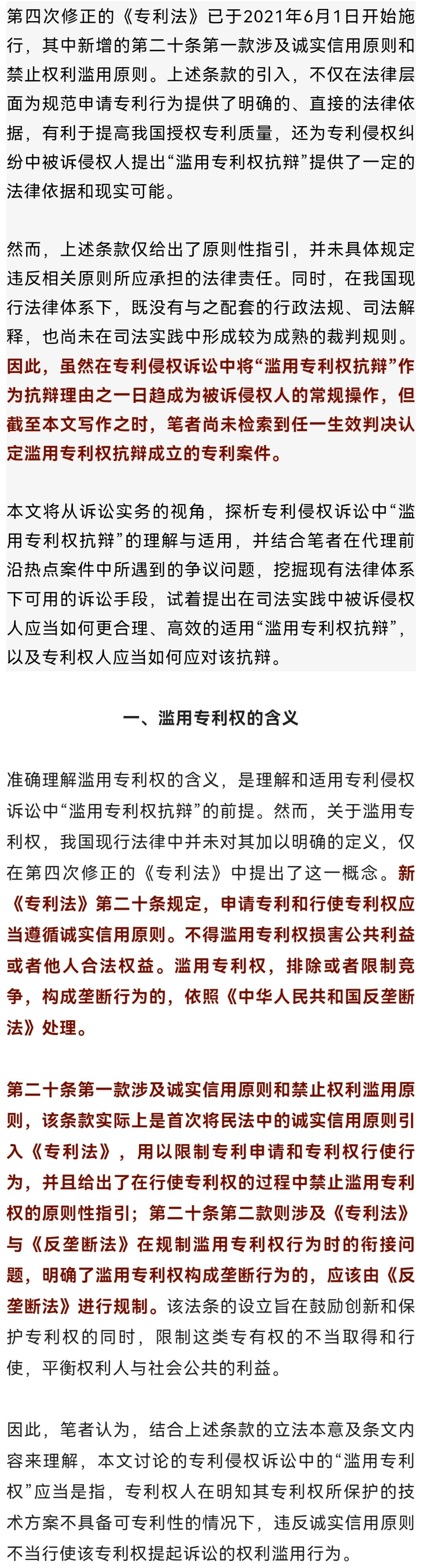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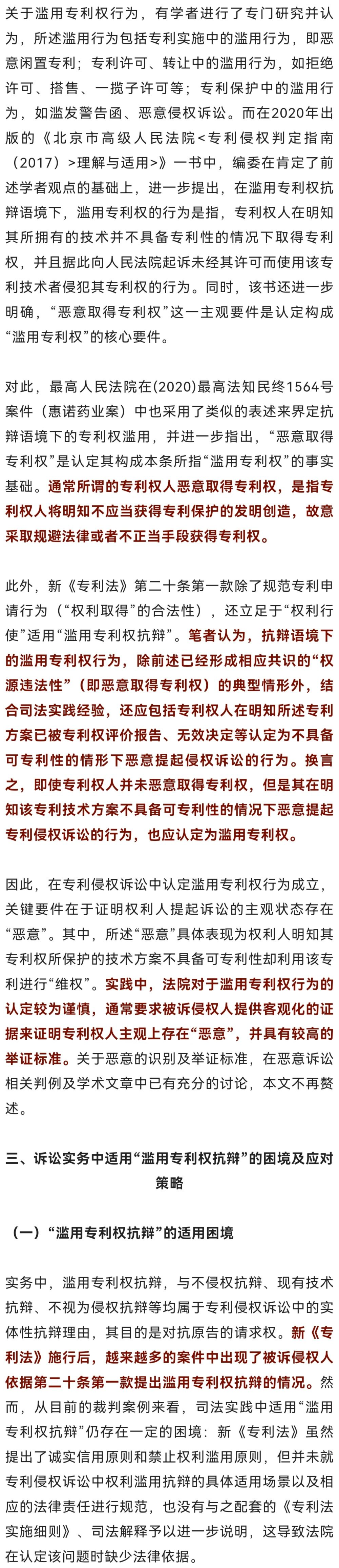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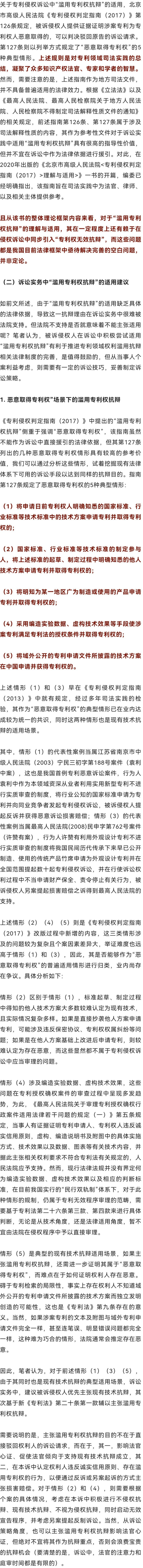
2. “恶意行使专利权”场景下的滥用专利权抗辩
专利侵权诉讼中的滥用专利权行为,除“权源违法”的“恶意取得专利权”的场景外,还存在“权源合法”但“恶意行使专利权”的场景,即,虽然专利权系通过正当手段取得但诉前明知所述技术方案已被专利权评价报告、无效决定等认定为不具备可专利性却仍然恶意提起诉讼的情形。代表性案例当属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5)京知民初字第1446号案件(远东水泥案)。四方如钢公司作为拥有多项专利权的企业,熟悉专利相关法律法规,其在侵权诉讼之前的无效程序中主动修改了权利要求,却在之后针对远东水泥公司的侵权诉讼中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以修改之前的权利要求确定保护范围,缺乏诉讼的权利基础,远东水泥公司另案起诉主张因其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损害赔偿,获得法院支持。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上述“恶意行使专利权”的情形,被诉侵权人应当在应诉过程中及时查询涉案专利的审查档案,确认该专利是否存在无效案件、是否出具过专利权评价报告,并作为利害关系人调取无效案卷资料、评价报告以确认专利的有效性,并在诉讼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况分别提出专利权效力抗辩、现有技术抗辩,同步启动无效宣告程序。同样,如果存在权利人“明知”的情形,也可以在诉讼中提出滥用专利权抗辩,认定权利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存在滥用专利权的行为,以便通过反诉或另案起诉的方式主张损害赔偿。
(三)诉讼实务中“滥用专利权抗辩”的应对
新《专利法》第二十条第一款涉及的诚实信用原则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虽然目前暂时不足以支持“滥用专利权抗辩”理由成立,但是其作为提起恶意诉讼损害赔偿反诉或另案起诉的威慑力是存在的。此外,目前被诉侵权人在应诉过程中将“滥用专利权抗辩”作为抗辩理由之一已成为常规操作,随着司法判例的累积,不排除部分法官会产生在个案中适用上述原则性“兜底”条款的冲动,从而在司法实践中逐渐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裁判规则,这一过程会促使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进一步完善。
因此,笔者认为,权利人在诉讼中应对“滥用专利权抗辩”时,第一要务是实事求是的评估自己提起的诉讼是否存在明显的“恶意”从而有可能被认定为“滥用专利权”。如果确认存在被认定为滥用专利权的可能性,则及时撤回起诉,避免被驳回诉讼请求的同时还被要求反赔。如果经评估,认为不存在明显的“恶意”,则应当重点应对被诉侵权人提出的不侵权抗辩、现有技术抗辩、不视为侵权抗辩,当这些抗辩理由较难成立的情况下,滥用专利权抗辩也不攻自破。
具体地,针对不同的情形,滥用专利权抗辩的应对可以包括但不限于:
(1)基于现有技术抗辩相同的理由,滥用专利权抗辩理由也不能成立;
(2)专利权被宣告无效的,不宜轻易认定为滥用专利权,本案中被诉侵权人没有举证证明权利人存在明显“恶意”;
(3)编造实验数据、虚构技术效果等问题涉及权利要求是否得到说明书支持、说明书是否公开充分等问题,其属于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第四款规制的范畴,应当在无效程序中认定,不属于侵权程序的审理范围;
(4)被诉侵权人的主张缺乏具体适用的法律依据,《专利侵权判定指南2017》不具有普遍适用的法律效力,不应予以考虑等。
四、结语
当前,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有效遏制侵权行为仍是各级人民法院的首要任务,在这一大背景下,对于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不宜因为存在权利滥用的可能而限制权利人行使诉权。在法律法规尚未就“滥用专利权抗辩”问题予以具体规范的情况下,专利侵权诉讼中不宜轻易认定专利权滥用,确有滥用专利权情形的,被诉侵权人可以依法提出损害赔偿反诉或另行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