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几天内已经有不少解读文章,不过大多数仅限于表面的文字解读,或者从监管角度为修订内容进行说明或背书。笔者曾长期就职于几家处于行业龙头的跨国企业,从事专职律师后亦继续为更多处于行业领先地位的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因此始终密切关注《反垄断法》的制订、实施和修改,并曾经多次参与《反垄断法》制订前的立法研讨和实施后的专题讨论。因此,笔者想从企业合规角度对《反垄断法》的最新修订做一个较为深入的解读,希望对从事企业法律顾问工作的同行们在进行反垄断合规审查时有所帮助,并期待与业界同仁进行更多探讨和交流。反垄断法是维护市场竞争秩序、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基础性法律,带有很强的政策性色彩,因此往往对整个行业的发展以及行业内龙头企业的运营有着根本性影响。从企业角度来看,本次修订的最大特点就是对平台经济实体垄断行为的规制和对纵向垄断协议实施“安全港”制度。前者对于大型互联网平台企业具有非常明显的影响,必将引起互联网平台企业内部法律顾问和管理层的高度重视;后者则是对各行业领先企业在规范管理营销渠道和销售活动方面的一次政策性“松绑”,有利于企业更好地管理不同营销渠道和经销商之间的竞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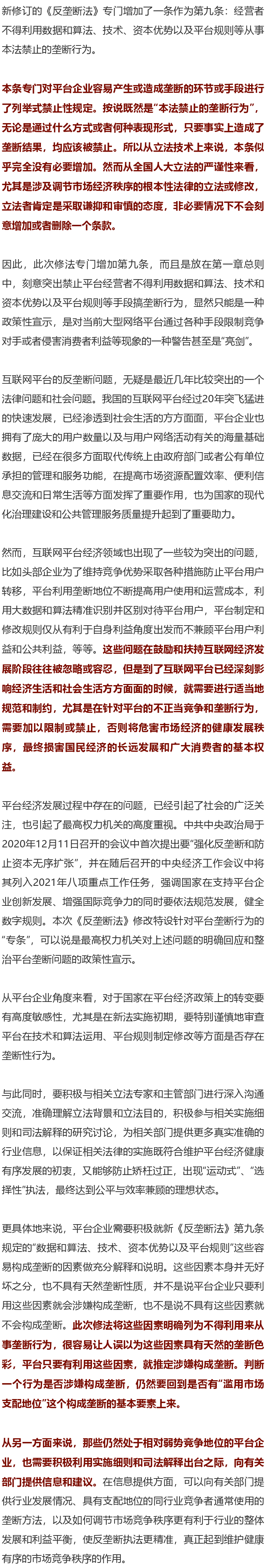
纵向垄断协议是指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之间达成的垄断协议,一般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二是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
《反垄断法》修改之前关于禁止纵向垄断协议的规定在第十四条:
这一规定简单明了,属于典型的“行为犯”,即只要有此类行为即属违法,因此十分有利于执法,从而成为套在各行业头部企业的一道紧箍咒,也是《反垄断法》自2008年8月1日实施以来最经常被引用于执法的一个条款,以致很多大型企业法务在进行合规审查时对此条款畏之如虎,战战兢兢,不敢越雷池半步。
以汽车行业为例,汽车制造商为了维护国内市场价格的统一,防止经销商之间恶性竞争,往往会对汽车零售价格进行统一规定。而这一点恰恰触犯了《反垄断法》关于纵向价格垄断的禁止性规定。仅在2014年,国家发改委就对多家汽车生产商进行突击检查,并以价格垄断为由处罚包括奔驰、大众和12家日本汽车零部件生产商在内的多家汽车制造企业,罚款超过15亿元人民币。以致欧盟商会于2014年8月发出一份特别声明,认为中国以汽车行业为重点的反垄断措施并不公正,美国商会也于2014年9月发布报告关注中国日益严格的反垄断执法行动。可能正是意识到反垄断行政执法领域存在的过度执法现象,一些地方法院在审理涉及“限定向第三人最低转售价格”的民事诉讼案件中,发出了不同声音。如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2012)沪高民三(知)终字第63号民事判决中认为:在对限定最低转售价格行为性质的分析判断中,相关市场竞争是否充分、被告生产地位是否强大、被告实施限定最低转售价格的动机、限定最低转售价格的竞争效果等四方面情况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78号指导案例北京奇虎科技有限公司诉腾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纠纷案和第79号指导案例吴小秦诉陕西广电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捆绑交易纠纷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均重点审查了被告是否具有市场支配地位以及被告的行为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从各行业的市场竞争格局来看,国内市场除了禁止或者限制民营企业进入的行业被几家国企高度垄断之外,多数行业实际上处于充分竞争状态,每个行业都有众多企业在市场上互相拼杀,只有极少数领域存在真正的垄断者(包括本次修法重点监管的互联网平台服务领域)。在这种激烈的市场竞争格局下,一个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对其产品或服务价格进行管控,恰恰有利于市场价格的透明化,维持企业及其经销商的合理利润空间,而不是任由有实力的经销商垄断部分市场,先通过恶性价格竞争扼杀竞争对手,再通过提高产品或附加服务的价格将成本转嫁给最终用户和消费者。一定程度的价格管控还有利于维持市场的整体竞争平衡,有利于消费者对于一定的价格所对应的产品或服务质量形成稳定的认知和预期。总之,纵向价格管控并不一定会造成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垄断后果,反而可能有利于维护正常的市场竞争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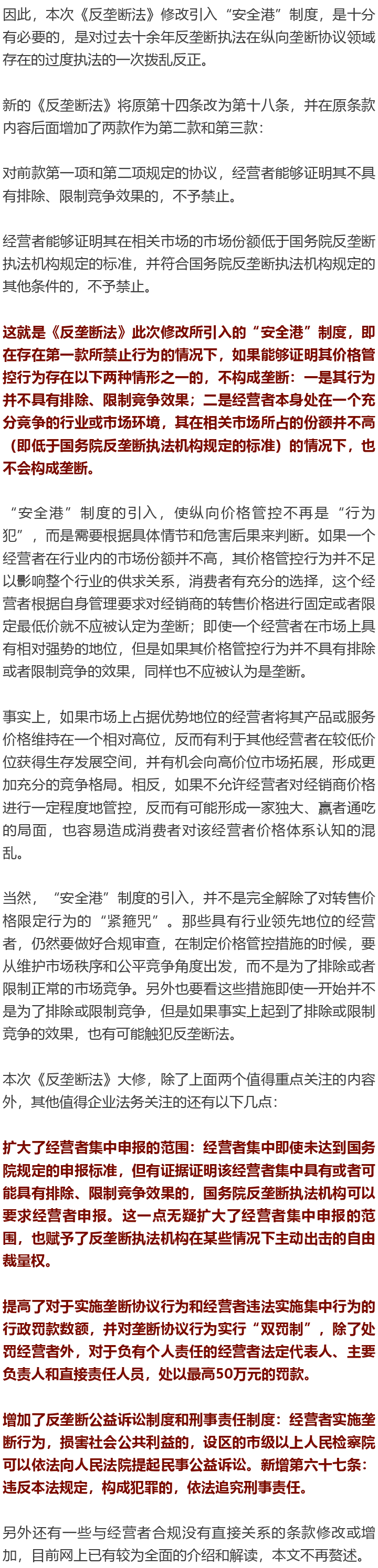
来源:万慧达知识产权